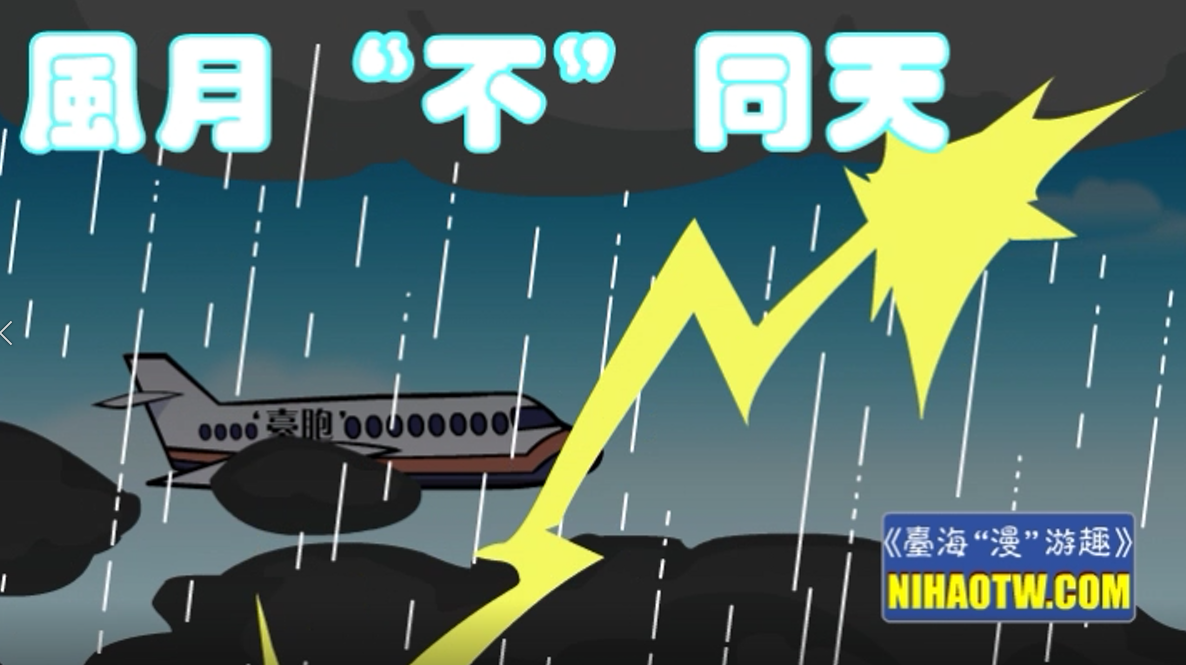“君子”無疑是先秦各家爭鳴議題中極為重要卻又眾説紛紜的核心概念之一。其中儒家最為強調君子的內涵價值,《論語》《孟子》《荀子》等經典提到“君子”一詞多達上百處。值得注意的是,在先秦儒家話語體系中,對君子內涵的認知卻出現了“君子訥言”與“君子必辯”這兩種似乎截然相悖的觀點。
孔子在《論語�裏仁》篇中説:“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訥言敏行成為孔子言論觀中最為經典的論點之一,謝良佐解釋道:“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孔子還多次在不同語境下提到“訥言”的問題。孔子崇尚少説多做,尤其重視慎言,反對巧言,比如“巧言亂德”(《論語�衛靈公》),“巧言令色,鮮矣仁”(《論語�學而》),“剛、毅、木、訥近仁”(《論語�子路》),將“訥言”與仁德緊密聯絡,表明對訥言的明確態度。綜觀孔子對“君子訥言”的態度,大致可以總結出三個觀點:
一是從言的本體出發,指出君子訥言的必要性。孔子説:“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論語�子張》)由於君子的言語能夠直接反映自身的修為,所以訥言在這裡就有兩層意涵,一則意味著言説須謹慎,二則意味著言説須立誠,與《易傳》“修辭立其誠”的觀點一以貫之,並影響到後世文學、美學理論的發展成熟。孔子不但要求君子自身須“訥言”,而且認為:“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論語�季氏》)這就從敬畏聖人之言的角度,反過來強調君子“訥言”的必要性。
二是將言與行結合,指出君子訥言的目的性。孔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論語�學而》)在於強調君子在學習上要行事勤勞敏捷,言説謹慎小心。孔子強調行先言後,將言行合宜與否視為做君子是否合格的重要標準,“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論語�憲問》)。所以當子貢問什麼是君子時,孔子回答説:“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論語�為政》)不僅要求君子言説要有目的性,還強調言説有可操作性,達到言出必行。這和《禮記》中的“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禮記�雜記下》),“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禮記�緇衣》)等觀點一氣貫通。
三是將言與禮結合,指出君子訥言的合理性。孔子認為言説的內容、時機都需要符合禮的要求,都是君子養成的重要內容。比如孔子説:“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意指不合禮儀的事不可以言説,將是否合乎禮作為言説內容的標準。從言説的時機來説,孔子認為:“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論語�季氏》)侍奉君王時,該言説的時候就要直言不諱,不該言説的時候就要保持沉默,言説要注意時機,也就是要符合禮的要求。
進入戰國時代,諸子百家一改春秋時期較為溫和的傳道態度,進而採用更為激進的話語方式。名家、墨家、縱橫家等學派從各自所屬的利益集團訴求出發開展論辯,進而影響到本來遵循“訥言”傳道方式的儒家。墨子直接向儒家發難:“儒者曰:‘君子必古服古言然後仁。’應之曰:‘所謂古之言服者,皆嘗新矣,而古人言之服之,則非君子也。然則必服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後仁乎?’”(《墨子�非儒》)墨子的這番論辯,以彼之道還施彼身,在邏輯上諷刺並否定了當時儒者以古為尊、故步自封的論點,從而客觀上通過論辯使得君子的含義得到豐富。
此時的儒家代表人物無疑是孟子和荀子,孟子被稱為“好辯”,孟子的時代“聖王不作,……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孟子�滕文公下》)。從孔子繼承而來的儒家學説在戰國紛爭時顯示出式微之態,孟子為了儒家能夠佔有一席之地,不得不改變孔子的傳道方式,轉而以鋪陳推演的比喻和雄辯為儒家爭得一方利益。故而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説,距�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孟子也從言説的角度描述君子:“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盡心下》)所謂言近而指遠,雖依然能看出孟子對孔子“巧言亂德”觀念的承襲,但已肯定君子言説的正面意義。
荀子相比孟子更進一步,他直截了當提出“君子必辯”的觀點,集中體現在《荀子�非相》一章中,荀子三次提到“君子必辯”,並提出了幾對概念,一是“姦言”和“仁言”,二是“腐儒”(“鄙夫”)和“君子”,三是“小人之辯”和“士君子之辯”,荀子通過這幾個概念構建起了“君子必辯”的理論框架。針對當時諸子爭鳴論辯,他首先從儒家學派外部著眼,指出“凡言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姦言”,凡是和先王禮義相違背的論辯之言,即使能言善辯,但是出發點錯誤,都是“姦言”,“君子不聽”,應予以否定,而“合先王”“順禮義”正是儒家學説的根本出發點,進而否定其他學派,是小人,非君子;其次再從儒家學派內部著眼,對不善言説之人也加以貶斥,皆為“鄙夫”“腐儒”,王先謙《荀子集解》註釋道:“腐儒,如朽腐之物,無所用也。引《易》以喻不談説者。”進而否定儒家學派中的過時觀點,指出凡是“不好言,不樂言”的“訥言”之人也非君子,此種“訥言”已不再值得推崇。
那麼,怎樣才是真正的君子呢?荀子亮出觀點:“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為甚焉。”在他看來,在堅持“法先王,順禮義,黨學者”的前提下,好言、樂言,敢於論辯之人才是真誠的君子。同時,荀子又採用儒家經典的二元對立方法,將君子與小人相類比,“小人辯言險而君子辯言仁”,引出“士君子之辯”和“小人之辯”的討論,君子和小人論辯的最大不同,就在於“士君子之辯”是經過先慮早謀,從而説出的“文而致實,博而黨正”的“仁言”,“小人之辯”是“詐而無功”的詹詹“姦言”。
荀子在《正名》篇進一步解釋何為“士君子之辯”:“辭讓之節得矣,長少之理順矣,忌諱不稱,祅辭不出,以仁心説,以學心聽,以公心辨。不動乎眾人之非譽,不治觀者之耳目,不賂貴者之權勢,不利傳辟者之辭,故能處道而不貳,吐而不奪,利而不流,貴公正而賤鄙爭,是士君子之辯説也。”與孔子所説的“剛、毅、木、訥近仁”不同,荀子認為辯言也是仁的外顯方式,以“仁心”為出發點去言説,以公正之心去辯論,“公心”也就意味著仁義之心。雖然荀子對儒家的“訥言”學説也予以一定的回護,他認為即使是必辯的君子,如果言説不仁,也要“則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辯不若其吶也”,但是這事實上與孔子對君子的認知已經發生了一定的區別。
相比于孔子與“敏行”相對的“訥言”觀點,荀子並非完全否認,而是進行適當批判。彼時儒家弟子大概一味固守成規,將“訥言”加以絕對化,視為對一切論辯都加以回避和否定,以至於在諸子之中逐漸喪失話語權,而荀子清楚認識到,如果不掌握話語權,儒家學派終究要在此消彼長的百家爭鳴之中消亡。是故,荀子一方面高擎“君子必辯”大旗,鮮明地改革儒家學派的理論觀點,另一方面,他在堅持以仁言辯説的必要性基礎上,也承認“訥言”的合理性。從而在不完全否定師尊孔子觀點的基礎上,既“法先王,順禮義”,向旁門爭奪儒家話語權,又團結本學派成員,達到“黨學者”的效果。
在對待“言”的問題上,經由孟子再到荀子的努力,戰國時期儒家的言論觀以及君子觀逐漸發生了變化。改變孔子時代重行輕言的觀念,“言”的價值提高,“不好言,不樂言,則必非誠士”;通過“辯”來體現“言”的意義,將“辯”視為從小人到君子再到聖人的進步途徑;以“仁”的判斷標準確立辯言的正統性和合理性,並將“辯”視為傳達“仁”的重要手段;以是否好辯,是否好言、樂言作為評價君子的重要準則。從而完成了從“君子訥言”到“君子必辯”的轉向過程。
(作者:史哲文,係安徽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安徽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