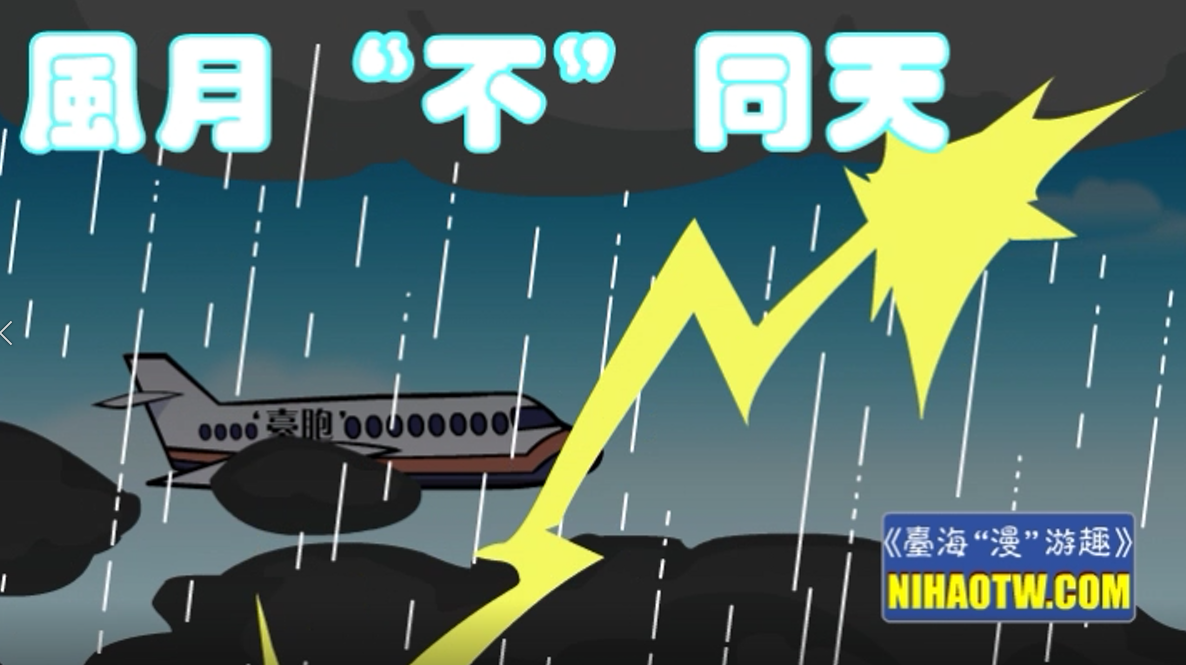法國作家都德在《最後一課》中,真實刻畫了阿爾薩斯人對法語和法蘭西祖國深摯的愛。但近年來,一些質疑之聲認為,阿爾薩斯-洛林人從血統、語言和文化上都跟德國人接近,普法戰爭時該地區已廣泛使用德語,德當局並無推行取消法語教學的必要,都德的文學創作並不符合史實。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中華文化教研部講師王凱歌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時指出,歷史上阿爾薩斯-洛林人的民族歸屬問題,反映出法德兩種不同民族觀念與民族國家建構模式的衝突。法國強調在現存國家領土範圍內的全體國民基於政治共識的同一認同,其民族國家構建過程具啟示意義。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有學者指出,阿爾薩斯與洛林地區真實的語言情況與都德《最後一課》文中所描述的情況存在反差。阿爾薩斯-洛林人語言、文化和身份認同的真實情況究竟怎樣?
王凱歌: 真實的語言情況與都德文中所描述的情況有些反差。由於長期的歷史文化影響,阿爾薩斯-洛林人從血統、語言和文化上都跟德國人接近。他們説德語,信奉新教路德宗而非法國人的主流信仰天主教,用德語出版,與德意志地區保持著緊密的聯絡。在大革命前,這兩個地區經常受到德國封建領主的干涉。然而,阿爾薩斯-洛林人更認同自己是法國人而非德國人。甚至在德國佔領當天,就有3000多名阿爾薩斯與洛林的年輕人潛逃至法國。
從歷史來看,阿爾薩斯-洛林問題可謂法德之間的千年問題。從9世紀中期開始,該地區就成為法德兩國(德國與法國的前身——東法蘭克與西法蘭克王國)爭奪的對象。圍繞阿爾薩斯與洛林的歸屬問題,法德兩國結下世仇。在法國大革命期間及之後的帝國政府,以及在德國佔領期間,法德都在該地區推行法國化與德國化的政策。二戰之後,法德和解,共同發起成立歐洲煤鋼共同體,阿爾薩斯-洛林問題才得到徹底解決。
中新社記者:既然血緣、語言與文化上都更像德國人,為何阿爾薩斯-洛林人建立了如此強烈的法國認同?
王凱歌: 這裡引申出一個理論問題,民族認同或身份認同到底是建立在什麼基礎之上?是建立在共同的血緣、族裔、語言與文化等生物指標的天然紐帶之上,還是建立在共同的政治信念、政治實踐與政治記憶等現代國家的建制經驗之上。
這反映出近代兩種不同的民族觀念,兩種不同的民族國家建構的模式。前者形成與成熟于18世紀末到19世紀中葉的法國,大體上把“民族”(nation)理解為一國的全體國民,相當於“國族”的概念。不管血統、族裔、語言、文化傳統上的差別,整體國民構成一個整體民族,可以稱之為“國家民族主義”(state nationalism),強調在現存國家領土範圍內的全體國民基於政治共識的同一認同。後者形成于19世紀後期的德國,把“民族”視為在語言、文化、血統等生物指標上具有一致性的群體,相當於“種族”的概念,可以稱之為“種族民族主義”(ethnonationalism/ ethnic nationalism)。
政治認同與共同的政治記憶超越了種族血統觀念,塑造了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法國大革命之前,王朝國家統治下的法國人並沒有同一的法蘭西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在法國大革命的鍛造與淬煉下,法國人形成了“我們的祖先是高盧人,我們的祖國是法蘭西”的民族國家認同,國家與民族成為一體,法蘭西民族最終取代法國國王成為認同的對象。
為了解決法國封建貴族與第三等級之間的階級矛盾,為了整合所謂法蘭克人後裔(封建貴族)與高盧羅馬人後裔(第三等級)之間的族群差別,啟蒙思想家盧梭提出了以“公意”(general will)構建社會公約的國家建構模式,同時也是法蘭西國族建構的方式。法國國境範圍內的所有人民通過社會公約鍛造了一個作為大我的法蘭西民族,從此,個體公民的小我就融入這個集體大我之中。這實際上將“人民”等同於“民族”,這樣就將主權從原來的國王手中交到人民手中(人民主權)。經過教士西耶斯的系統論述,“民族”(nation)又具有了“聯合的意願”和“自主掌握自己命運的自由人整體”的含義。可見,大革命時期,法蘭西民族是一種“政治民族”的構造,表達了“政治聯合體的意識”。
在這樣一種國家建構之中,民族建構不是基於相同的族裔、血統、語言與歷史文化傳統,而採用“族國同構”的“國家民族主義”模式。這實際上是現代國家的公民認同取代基於血統的、族群的、地方的身份認同。正如1789年國民公會的一次辯論中,一位革命者談及猶太人地位時所説:“對作為個人的猶太人,我們給予(國民應有的)一切。對作為一個民族的猶太人,我們什麼也不給。”這就可以理解為何生物學意義上更接近德國人的阿爾薩斯-洛林人更認同自己是法國人。
法國大革命時,被馬賽人傳唱至全法國的《馬賽曲》正是阿爾薩斯人魯熱�德�利爾為抵抗入侵的普奧干涉軍而作的《萊茵軍團戰歌》。在戰勝普奧聯軍的決定性戰役瓦爾密大捷中,功不可沒的法軍指揮官凱勒曼也是阿爾薩斯人。阿爾薩斯-洛林與法國其他地區一起接受了大革命的洗禮,一起參與了反抗外來侵略的共同鬥爭,在革命和第一帝國時代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社會上升空間與政治權利。
德國政治學家馬克斯�韋伯認為,阿爾薩斯居民的法蘭西情結説明決定民族忠誠的最核心要素是共同的政治記憶。這種(法蘭西)共同體的情感來自共同的政治經驗,以及間接的社會經驗,人民大眾在心中高度評價那些被看作摧毀封建制度的象徵性事件,有關這些事件的故事取代了原始英雄傳説的地位。
中新社記者:英國政治學家塞繆爾�芬納在《統治史》中指出,“在從王朝國家向主權國家轉變的偉大政治試驗中,法國人發明了民族主義這種現代意識形態。”在這場“試驗”中,法國採取了哪些現代國家構建措施?
王凱歌: 首先,確立法語作為法蘭西民族語言的地位,使各族群獲得同一的身份認同。在法國革命前,根本不存在法蘭西民族,只有效忠法蘭西國王的布列塔尼人、普羅旺斯人、諾曼底人、阿基坦人、洛林人、阿爾薩斯人、勃艮第人等。當時的法蘭西王國也沒有統一的語言,各地説自己的方言。甚至到1863年,根據法國的官方調查,還有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國民是不説法語的。為此,法國革命政府及此後的帝國政府都毫不妥協地強推“法語化”政策。
其次,在學校各個年級教授標準的歷史教材,以法蘭西歷史上的英雄事跡與愛國美德教育學生,培育他們的民族自豪感。《最後一課》就是這種觀念背景的産物,是通過文學和歷史教育塑造國民愛國主義和民族情感最成功的典範。正如美國學者尤金�韋伯的《從農民到法國人》中指出的,到19世紀下半葉,通過普及義務教育與普遍義務兵役,法國才成功地將西部、東部和中南部地區的農民改造成為法國人,這首先歸功於強有力的中央集權政府。
再次,塑造民族認同的符號、象徵與儀式以增強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強化民族記憶。大革命後,法國政府建立先賢祠,將伏爾泰、盧梭等啟蒙先賢安葬于其中,樹立聖女貞德作為反抗外來侵略的民族圖騰,把拿破侖樹立為民族英雄,作為共和革命精神的象徵,以“法蘭西的名義”將其骨灰迎入榮軍院等。此外,一系列與法蘭西民族主義精神相關的節日如最高主宰節、自然節、人類節與法國人民節被確立下來。這些政策增強了法蘭西民族的凝聚力與向心力。
這充分表明,政治民族(或國族)是需要中央集權式的國家強力自上而下地構造的。將領土範圍內的全體人民鍛造整合成一個政治民族是現代民族國家構建的題中之義。沿襲自舊制度的法國中央集權制傳統更是便利了現代法蘭西民族的構造,而這種國族的構建是基於法蘭西共和革命的一系列價值認同之上。
中新社記者:法國民族觀念與民族國家建構模式在今日有何體現?對中西文明互鑒有何啟示?
王凱歌: 今日,面對移民化與宗教極端主義、多元主義潮流的衝擊,法國依然沿襲“國家鍛造民族”的傳統精神,以應對日益嚴峻的移民社會多樣化宗教與族群的挑戰。今年初,法國穆斯林信仰委員會(CFCM)宣佈,各組成團體已經同意總統馬克龍此前要求其制定“共和國價值憲章”的最後通牒。該憲章致力於根除極端主義。CFCM主席穆罕默德�穆薩維表示,“該憲章重申了穆斯林的信仰與共和國原則的兼容性,這些原則包括世俗主義,以及法國穆斯林對其公民身份的承諾。”
從法國民族國家的建構歷程尤其是從阿爾薩斯-洛林人的法國認同來看,現代國家建構的基礎是一個致力於建國的“政治民族”(族國同構),這需要強力的糾合。為建立現代國家而構造的民族是政治民族,即“國族”(state nation)。在民族國家建構的整合之下,自然個體演變成民族成員,全體人民等同於國族。而在這個國族之下,不應再有政治民族的分野。小我融入大我之中,個體只能在整體中獲得其價值與意義。可以説,法國的民族國家構建過程給我們提供了重要經驗與啟示。(完)
王凱歌,中央社會主義學院中華文化教研部文化比較教研室教師。2011年本科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修讀政治學理論;2014年碩士畢業于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修讀政治學理論,獲法學碩士學位;2018年博士畢業于北京大學哲學系,師從杜維明先生,修讀中國哲學,獲哲學博士學位。研究領域包括中西方政治思想史、儒家情感哲學、中國哲學史、中西方比較哲學等。(中新社記者 安英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