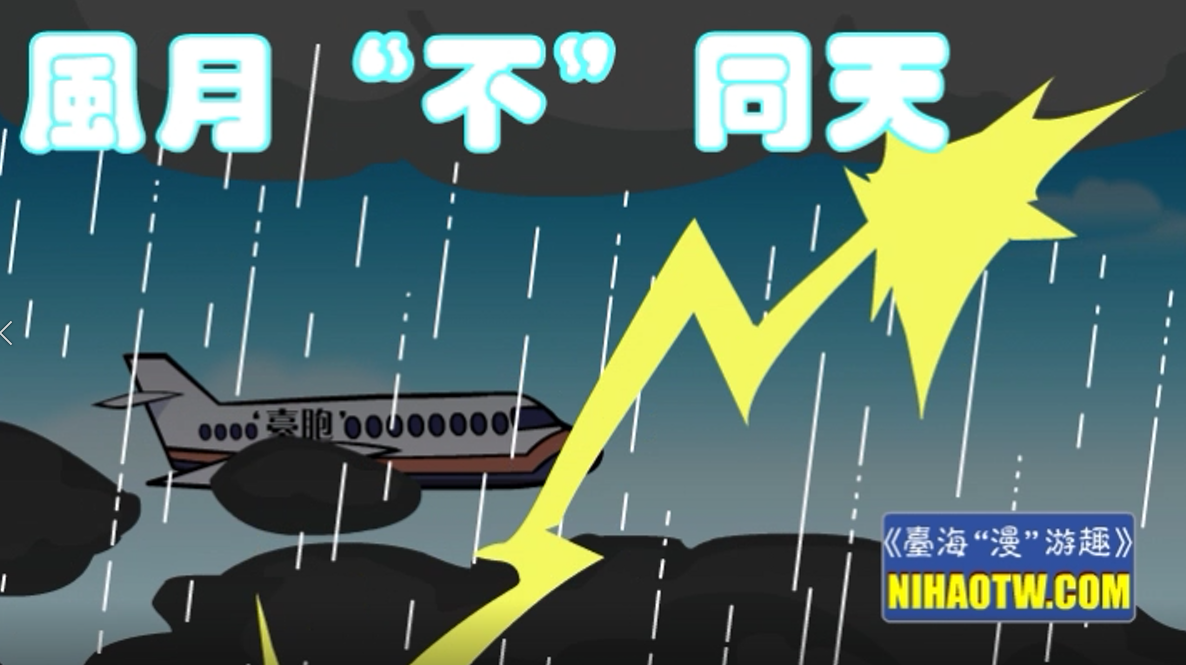“風在吼,馬在叫,黃河在咆哮……”
“北風那個吹,雪花那個飄,雪花那個飄飄,年來到……”
無論何時何地,當這些樂曲聲響起,總有人會跟著哼唱。因為,這些音符,已經成為民族基因裏的紅色印記。
80多年前,在中國共産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感召下,大批愛國知識青年和藝術家奔赴延安。他們與長征而來的文藝戰士、陜北紅軍中的文藝戰士一起歌唱、寫作、演戲、作畫,為抗日救亡提供了豐富的精神彈藥。
他們到戰鬥前線去、到老百姓中去,播撒革命文藝的火種。
硝煙瀰漫中,延安文藝奏響全民族奪取抗戰勝利的凱歌。
回溯歷史,我們探尋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的精神源泉。
《黃河大合唱》,毛澤東連讚三聲“好”
延安的天是藍藍的天,夏日暖陽照在魯藝舊址的東山上。
這裡是冼星海來到延安魯藝的第二處住所,很多經典作品就誕生於此。
1939年春,剛來延安不久的冼星海就在北門外的魯藝駐地用六個晝夜完成了《黃河大合唱》的全部譜曲。
在抗日戰爭最焦灼的危難關頭,這部民族交響史詩激勵了中華兒女奮起抗爭、保衛祖國的勇氣和信心。
當時,他只有34歲。
1905年,冼星海出生在一個貧苦漁民家庭。父親早亡,靠著母親微薄收入和勤工儉學,冼星海輾轉新加坡、廣州、北京、上海,追尋音樂夢想。
彼時,中華大地軍閥混戰、外敵入侵、民不聊生,24歲的他寫道:“學音樂的人啊,不要太過妄想,此後實際用功,負起一個重責,救起不振的中國,使她整個活潑和充滿生氣。”
為了精進音樂技巧,冼星海再次遠渡重洋求學。在法國巴黎,他窮困極了,幾次饑寒交迫昏倒在巴黎街頭。
“在困苦生活的時日,對祖國的消息和懷念也催迫我努力。”“在悲痛裏我起了應該怎樣去挽救祖國危亡的念頭。”“我把對於祖國的那些感觸用音樂寫下來,像我把生活中的痛楚用音樂寫下來一樣。”在冼星海的回憶文章中我們看到了這位年輕的音樂家如何頑強地度過留學歲月。
從法國巴黎音樂學院畢業後,冼星海回國即投身於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歌�運動。全面抗戰爆發,他隨救亡演劇二隊從上海到武漢,邊創作邊演出。哪有群眾,冼星海就到哪去;哪有冼星海,哪的抗戰歌聲就更加高昂。
1938年,冼星海偶然讀到了《抗戰中的陜北》一書,頓覺心底明亮。他興奮地對妻子錢韻玲説:“中國現在已成了兩個世界,國民黨反動派完全墮落了,延安才是新中國的發源地!”
“我們走吧,到延安去,那裏有著無限的希望和光明!”
那時的延安,已是全國抗戰文藝運動的中心。
文藝工作者一手拿筆,一手持槍,積極投身火熱的戰鬥生活,為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擂起戰鼓。
1938年,黨創辦的第一所綜合性藝術教育機構——魯迅藝術學院成立。同年,冼星海接到了魯迅藝術學院寄來的全體音樂系師生簽名邀請他去任教的信件。
到延安的第二天,冼星海就開始授課。他白天教課,傍晚經常提著馬燈,翻山越嶺步行十幾裏,到延安各處教歌。
1939年2月,冼星海去醫院探望在前線受傷的詩人光未然。兩位好友一拍即合,有了合作創作大型音樂作品的念頭。
病床之上,詩人將兩個多月以來穿越黃河,目睹船夫們與狂風惡浪搏鬥的情景與前線的戰鬥生活濃縮成400行長詩。
3月11日晚,冼星海應邀參加演劇三隊舉行的歌詞朗誦會。在一盞昏暗的油燈旁,25歲的年輕詩人激情飽滿朗誦完歌詞。冼星海激動地站起來,上前一把抓住歌詞説:“我有把握把它寫好!”
“早春的延安夜裏很冷。我們用一小盆炭火取暖,我有時看他寫得累了,就煮一點紅棗給他吃。那時候延安的木炭還是很缺乏的,夜深人靜時,炭火熄了,窯洞裏非常冷,但星海的創作熱情卻比火焰還要熾熱!”錢韻玲如此回憶。
1939年4月13日,《黃河大合唱》在陜北公學大禮堂首演。
那是個物質條件極度缺乏的年代。除了三四把小提琴外,就是二胡、三弦、笛子、六弦琴和打擊樂器。沒有譜架,就用木板搭起一個。沒有低音樂器,就用汽油鐵桶改造成低音二胡。還有用大號搪瓷缸裝著20多把勺子製成的新型“樂器”,發出“嘩啦嘩啦”之聲,與管弦、鑼鼓配合著合唱,烘托出黃河萬馬奔騰之勢。
樂器雖簡陋,激情卻滿懷。演出贏得了觀眾熱烈的掌聲。
大約一個月後,在慶祝魯藝成立一週年音樂會上,冼星海親自指揮100多人的合唱團演唱《黃河大合唱》。剛一唱完,毛澤東連聲稱讚:“好!好!好!”不久,周恩來看過表演後題詞:“為抗戰發出怒吼,為大眾譜出呼聲!”
延安魯藝文化園區管理辦公室主任劉妮説:“冼星海在延安成長為一名傑出的音樂家,也從一個愛國的民主主義者逐漸成長為一名忠誠的共産主義戰士,是思想上的飛躍帶來了藝術創作上的新高峰。”
當時的延安是一座革命的大學校。冼星海閱讀了大量馬列主義理論專著,聆聽毛澤東作的許多重要報告。理論學習使他“竟發現了音樂上許多的問題過去不能解決的,在社會科學的理論上竟得到解答”。
他産生強烈的入黨意願。
1939年6月14日,經組織批准,冼星海終於加入中國共産黨。他在日記中寫道:“今天就算我入黨的第一天,可以説是生命上最光榮的一天。我希望能改變我的思緒和人生觀,去為無産階級的音樂奮鬥!”
一年後,冼星海受命赴蘇聯,為大型紀錄片《延安與八路軍》進行後期製作與配樂。那時他的女兒冼妮娜還不到一歲,是冼星海心頭最重的牽掛。
“我常想念著你和妮娜,為著愛,我們更應加倍努力,我們要貢獻一切所有,為民族解放、為實現我們的最高的理想。望你珍重,小心愛護妮娜。讓我吻著你和她。”
“你身體好麼?妮娜好麼?唸唸!最近有西紅柿賣,你可多買一點來食,妮娜也要食一點,這是補血的,而且容易消化。”
……
在與妻子的通信中,冼星海對女兒的成長呵護備至。母女二人也在延安等待著他的歸來。
然而,在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冼星海的這次出差,竟成了與妻子女兒的永別。
冼星海一到蘇聯就遇上衛國戰爭爆發,回家的路被戰火阻隔。
常年的勞累,艱苦的戰爭環境,使他身染重病。1945年10月30日,冼星海的生命在異國他鄉落下休止符,年僅40歲。
毛澤東親筆為他題挽詞:“為人民的音樂家冼星海同志致哀!”
“在抗戰烽火中,如冼星海一樣,延安的文藝工作者始終將個人命運與國家命運緊密結合,文藝創作始終與時代主旋律同頻共振,成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劉妮説。
“黑古元”變成“白古元”
1938年,19歲的古元奔向革命熱土延安,開啟新生活。
“一到陜北革命根據地,非常鮮明突出地感到人民當家做了主人,多年的夢想在那裏實現了。雖然物質生活很艱苦,但上下級之間、軍民之間、同志之間關係平等融洽。人們對勞動和生活充滿感情、希望和信心。這些都深深感染著我。”古元回憶。
在陜北公學接受了三個月的革命理論學習後,古元正式進入魯迅藝術學院美術系學習木刻版畫。
那個年代,大多數群眾都是文盲。因此,圖畫宣傳更顯重要。
1940年古元被分配到延安縣川口區碾莊鄉,擔任鄉文教委員兼鄉政府文書。
碾莊共有42戶人家,全村只有一個識字的人,其餘都是文盲。古元在工作之餘繪製識字卡片,分發給鄉親們。過了很多天,細心的古元注意到,鄉親們把畫著公雞、牛、騾、馬、驢、羊的圖片都貼在墻上,而畫著水桶、鐵鏟、鐮刀的圖片,誰家也沒貼出。
他由此了解到老百姓對家畜的喜愛,也領會他們的審美情趣。
後來,他創作了《牛群》《羊群》《鍘草》《家園》4幅木刻,拓印很多張,分送給鄉親們。他們看見畫就津津樂道:“這頭驢真帶勁!這不是劉啟蘭家的大犍牛嗎?放羊不帶狗不行,要背上一條麻袋,母羊在山上下了羊羔裝進麻袋帶回了。”
每創作完一幅作品,古元都要分送給鄉親們。他們很喜歡這些作品,也對有些表現手法提出了批評:“為啥臉孔一片黑一片白,長了那麼多黑道道?”
從群眾的建議裏古元明白,他原先學習參考的西方木刻手法並不被老百姓理解,這促使他轉而學習傳統繪畫和民間年畫的創作手法。
“黑古元”變成“白古元”,鄉親們更喜歡他的作品了。
與鄉親們熟悉後,古元對他們産生了深厚的感情。看見鄉親們的日常生活,如同見到優美的圖畫一樣。
政府辦公室是古元最常待的地方,老百姓隨意進出、毫不拘束。他們有的將鋪蓋卷往地上一擱,揣著手跨坐在凳子上找工作人員開介紹信,有的彎著腰、比畫著向工作人員訴説遭遇,還有的背著挎包、攬著衣服正準備進門,一條狗跟在身邊,顯然剛從遠方歸來。這些熟悉的場景,被古元刻畫進了《區政府辦公室》。
“作品中,老百姓姿態輕鬆隨意,工作人員神情專注認真。畫面的左下角,黑色桌子上一份《解放日報》格外顯眼。這就是邊區的日常生活,也是人民群眾當家做主的真實寫照。古元善於將黨的政策融入老百姓的生活中,將真實生活融于藝術中,以小切口反映大時代,歌頌新生活,是邊區生活的歌手。”劉妮説。
古元的另一幅作品《逃亡地主又歸來》被艾青評價為“邊區的史畫”。
畫面中,地主一家正在前行。地主老兩口騎在馬上,臉色陰沉,少爺佝僂身軀,體質虛弱,少奶奶懷抱幼兒,騎馬跟在身後,老長工牽著馬,走在最前面。遠處是黃土高原與窯洞。
當時,古元聽老鄉説附近田崖莊逃到“白區”的地主姚老大又回來了,立刻敏銳捕捉到地主歸來的意義。這正反映了當時土地政策的轉變。為了建立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後,中共實行減租減息的土地政策,提高農民的抗日積極性,聯合地主階級一致抗日。
一個政策、一段歷史,就這樣被古元巧妙地濃縮進版畫中,傳遞時代變遷和人們的思想變化。
回顧碾莊歲月,古元曾説:“我在碾莊工作和生活將近一年,時間不算很長,但這段過程是非常重要的,使我深切體會到為什麼作畫和怎樣作畫,它對於我以後的藝術道路有著深遠的影響。”
1945年4月,紐約《生活》週刊第一次向美國民眾介紹了中國現代木刻,所刊登的16幅作品中有彥涵、古元等人的6幅。文章的標題是《木刻幫助中國戰鬥》。來自中國黃土高原山溝裏的魯藝木刻不僅喚起了中國人民抗戰的熱情,也鼓舞了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鬥志。
對於延安歲月,他曾説:“如果沒有在陜北公學和魯藝所受的教育,是不能明確樹立為人民服務的牢固信念的。”
直至20世紀80年代,他仍對延安唸唸不忘:“我常想,如果我一直留在陜北,也許我的作品的泥土味會更濃,也就更具有特色,對祖國藝術的貢獻可能更大一些……體驗生活要深入,不能圖新鮮,要帶著熱愛生活的深厚感情去發掘和開採,要像母親永遠不會煩孩子一樣熱愛生活。”
從《東方紅》到《白毛女》,延安文藝永放光芒的奧秘
“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一曲《東方紅》,唱出了人民群眾對毛澤東和中國共産黨的款款深情。
在半個多世紀的流傳中,這首歌成為刻在國人文藝細胞中的紅色基因。
它的原創者是陜北佳縣一個普通的農民——李有源。
1942年冬天的一個早晨,李有源忽見東方一輪紅日噴薄而出。“把毛主席比作太陽是最好不過的。”有了這個想法,李有源隨即套用陜北民歌《騎白馬》的曲調哼唱起來:“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生存,他是人民大救星。”
後來經過魯藝人不斷整理、完善和提升,使它形成現在的版本,而且有了大型交響樂大合唱《東方紅》。
馬可稱李有源是他們走出“小魯藝”後遇到的最好的教員之一,在與這些農民藝術家和詩人交往中,他感慨:“可見藝術作品的提升,絕不只是一些專業技術的加工,更重要的是繼續深入思想改造,得深入生活,虛心學習民間藝術。”
延安時期的文藝工作者向民間文化尋求創作資源,把這種文化自信轉化為藝術形式,通過文學、音樂、美術、戲劇等各種藝術形式來展示“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形成了波瀾壯闊的“延安文藝”景觀。
李季長篇敘事詩《王貴與李香香》吸納了信天遊的旋律,張魯、關鶴童、安波、劉熾等人用陜北民間嗩吶曲改編出著名的《哀樂》,古元的版畫將西方創作手法融入中國傳統的、民間的審美……
大型歌劇《白毛女》則成為我國民族新歌劇的里程碑。
1944年,西北戰地服務團從晉察冀前線回到延安,帶回了“白毛仙姑”的民間傳説。聽到這個故事的藝術家們被深深感動,決定創作一齣大型歌劇:借由一個佃戶女的悲慘身世,展現“舊社會把人逼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的時代主題。
主創團隊經過認真討論,確立了這齣戲的總體要求:戲要寫真實生活,音樂創作要具有民間的泥土氣息和豪邁的民族氣勢,美術設計要有簡單明快的民族風格,要搞成一部既有民族特色又有時代氣息的大歌劇。
“方針定下來之後,我們一場一場地拉戲。我們談定一場戲,賀敬之就去整理,結構好,寫好歌詞,交給三位作曲家譜好曲,再交給每個演員去練唱。”地主黃世仁的扮演者陳強曾回憶説。
排練有時在魯迅藝術學院的操場上進行,看到的師生、勤務員、老百姓發現不合理、不夠好的地方就大膽提出來,不少都被劇組人員採納了。
如此細緻創作了三個月,1945年4月,《白毛女》在延安上演。前後共演出了30多場,有的人連看幾場,還有人大老遠地從安塞、甘泉趕來看。
抗戰勝利後,一部分魯藝師生將《白毛女》帶到了晉察冀地區,又演遍了整個解放區,極大地推動了解放戰爭和土改運動的進程。
延安大學魯迅藝術學院副教授趙宇濤説,《白毛女》在群眾中有極強的感染力,是因為它在群眾藝術實踐的基礎上創作。可以説它是中國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民族歌劇,採用了西方歌劇的作曲手法,融入中國傳統民間音樂的元素,對後期中國民間民族音樂的發展具有里程碑意義。
新中國成立後,歌劇《白毛女》被改編成電影、芭蕾舞劇、連環畫、京劇等多種藝術形式,譯成俄文、日文、英文等多種語言,遠播海外。今年,為慶祝建黨百年,重溫紅色經典,文化和旅遊部組織復排了民族歌劇《白毛女》等一批經典作品。
“時至今日,《白毛女》的時代價值不減。它誕生於抗日戰爭時期,反映的卻是土地革命的問題,生動體現了文藝引領時代進步的作用。它所揭示的主題思想——共産黨為民謀幸福的初心,穿越時空,歷久彌新。”劉妮説。(新華每日電訊記者 孫波、劉書云、蔡馨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