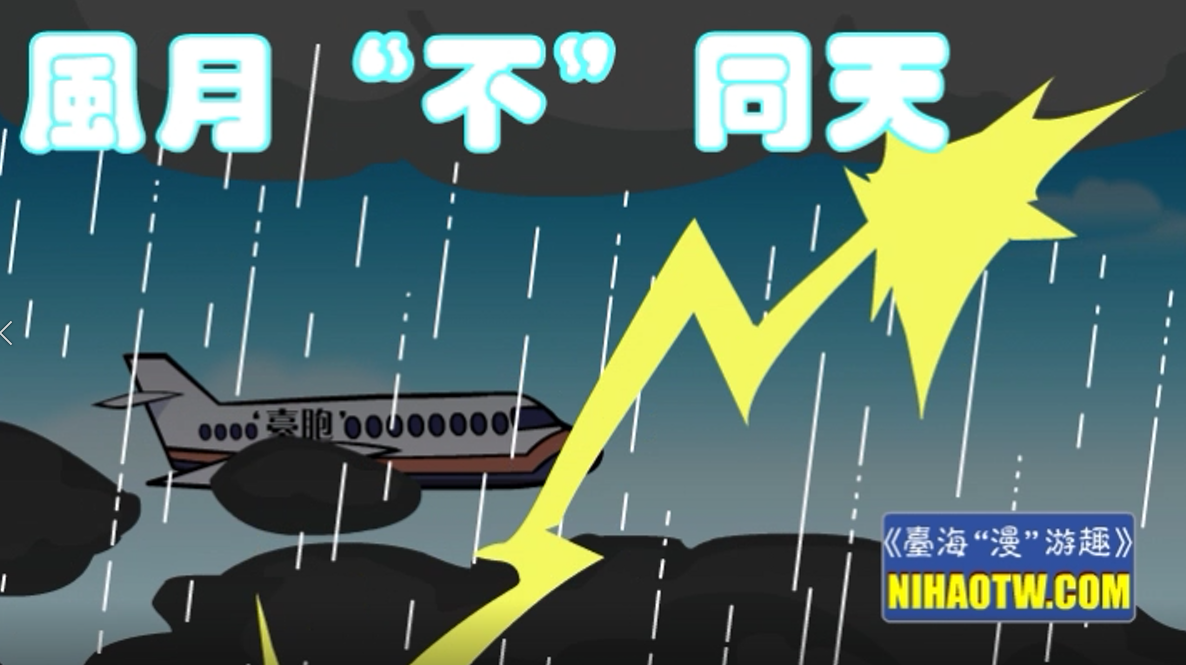元代王蒙《葛稚川移居圖》(局部),故宮博物院藏。中國古代留下諸多修仙煉丹軼事,此圖描繪東晉人葛洪攜帶家眷移居羅浮山,修道煉丹。
于賡哲
疾病戕害人體,謊言和騙術戕害人心,普通人憑藉一己之力也許對付不了病菌和病毒,但健康樂觀的心態、科學的頭腦,以及最重要的獨立思考的精神,能幫助我們抵禦謊言與騙術的襲擾。
自古疾病大概是戰爭之外最好的社會試金石,在疾病面前不僅有人類的善良,也有惡意與謊言,這種謊言有人需要,有人推動,有人接受,來自各個社會階層,受害者也分佈于各個階層。不是所有偏離事實的都是謊言,有的只是認識誤差,而有意的謊言卻經常和這種認識誤差一起,滲透進社會思想、組織結構、民風民俗之中,沉澱在歷史長河裏。謊言總伴隨疾病,因為疾病威脅之下,人的分辨能力最低,對生命的渴望使人的戒備心理降低,偏聽偏信,“死馬當作活馬醫”的心態導致到處抓救命稻草,給了謠言和騙子可乘之機。
騙術面前,人人平等,連秦始皇也是受害者。奮六世之餘烈一統天下的秦始皇,中年以後倍感人生苦短,但那時候還沒有明確的成仙思想,而是追求長生不老。很多人有疑問:那麼多術士為秦始皇求所謂“不老之藥”,這種註定要失敗的事情是怎麼瞞過以法令嚴苛著稱的秦始皇的呢?《東漢生死觀》一書中談到,術士們有解決之道,那就是為始皇帝設置不可能完成的前提條件,不完成則靈藥不靈,比如説秦始皇生活過於奢華,心不靜則法術不靈,而秦始皇不可能放棄奢華,也不可能做到心靜,術士也就得以暫時免責;或者開列極其苛刻的條件,騙了錢逃之夭夭,比如徐福就編造了蓬萊山海神嫌棄秦始皇禮薄,不給仙藥的故事,於是秦始皇“遣振男女(童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而徐福則成功卷款私逃。
《史記》卷6《秦始皇本紀》:“始皇帝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眾,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此事非常著名,史家多以此為當時微妙的權力關係之例證,但此事背後其實隱約有術士的影子,同卷前一段文字更值得注意:
盧生説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為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陵雲氣,與天地久長。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惔。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
盧生的行為模式與徐福如出一轍,他為秦始皇開列的長生前提條件就是:一要恬惔;二要“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一旦行蹤被人知曉,則真人不見,仙藥不得。皇帝不見外人,這就是一個幾乎不可能實現的條件,但秦始皇篤信不疑,改稱自己為真人,並下令宮室之間築造復道、甬道,有敢洩露皇帝行蹤者斬。故李斯削減車騎的行為等於告訴皇帝,有人向外洩露皇帝行蹤,導致藥效“破功”,從而引起了始皇帝的憤怒。這才是故事的“點”所在。
秦始皇對這些術士未必沒有疑心,但“合理化(rationalization)”的心理需求使得他甘心受其擺布,即製造“合理”的理由來解釋並遮掩對自我的傷害。在這個過程中,推諉(projection)機制發揮的作用最為明顯,即主動使用一些術士為他設置好的客觀原因為失敗尋找理由,從而繼續保持對行為合理性的信仰。但忍耐是有極限的,在術士盧生、侯生逃走並謾罵秦始皇之事發生後,就有了著名的“坑儒”事件,被坑者多數是尚未來得及逃走的術士。
以秦始皇之地位,尚且如此受愚弄,那普通民眾可想而知。數千年來民眾在疾病的威脅之下也曾被愚弄與擺布,邪教的盛行就是一個典型。每逢疫病時期,邪教就趁機大肆發展信眾,所採取的就是“渲染恐怖”加上“禳災祛病”的手法。例如東漢後期,從靈帝到獻帝長期的疫病流行,大大促進了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的發展,而疾病和祛病就是他們發展信眾、鞏固組織的重要工具,在此基礎上建立了擬國家化、軍事化的組織,這一點對漢代朝廷來説是極大的教訓,也就無怪道教人士對他們的批判了,如葛洪《抱朴子內篇》卷9:“曩者有張角、柳(劉)根、王歆、李申之徒,或稱千歲,假托小術,坐在立亡,變形易貌,誑眩黎庶,糾合群愚。”
三國以降曾有對聖水的崇拜,往往發生在瘟疫爆發時期:
《北史》卷27《李先傳》:(北魏)靈太后臨朝,屬有沙門惠憐以咒水飲人,雲能愈疾,百姓奔湊,日以千數。
《高僧傳》卷10《晉洛陽大市寺安慧則》:晉永嘉中,天下疫病,則晝夜祈誠,願天神降藥以愈萬民。一日出寺門,見兩石形如甕,則疑是異物,取看之,果有神水在內。病者飲服,莫不皆愈。
葛洪《抱朴子內篇》記載過以假充真的“聖水騙局”以及政府的應對。洛西有古墓,早已坍塌,內有積水,由於墓中多石灰,石灰汁主治瘡,有人在這裡洗瘡得愈,於是四方病患雲集,不僅洗,還有內服者,不久就出現了利用此墓斂財和搞淫祀的現象:“近墓居人,便於墓所立廟舍而賣此水。而往買者又常祭廟中,酒肉不絕。而來買者轉多,此水盡,於是賣水者常夜竊他水以益之。其遠道人不能往者,皆因行便或持器遺信買之。於是賣水者大富。”官府最後強行毀壞了古墓,制止了癲狂的民眾。
官府可能對騙取錢財的事情睜一眼閉一眼,但對於威脅到統治、蠱惑人心的邪教一貫是要遏止的。唐代聖水崇拜捲土重來,李德裕《會昌一品集》記載亳州忽然出現聖水,據説可治百病,立竿見影。南方百姓騷然,“自淮泗達于閩越,無不奔走”,“每三二十家即顧一人就亳州取水”,渡江人數眾多,防不勝防,水每鬥賣到三貫,且有歹徒以其他水冒充。李德裕命令填塞泉眼杜絕根本,並上報皇帝。
歷代統治者都警惕這種利用疾病的邪教。《朝野僉載》卷三記載,唐高宗時有妖人劉龍子以祛病為由妖言惑眾,作一金龍頭藏袖中,以羊腸盛蜜水,接在龍頭上,羊腸纏著胳膊藏在袖中。有求醫者則伸出龍頭,流出水來,號稱包治百病。斂財無數,隨著信徒的增多,此人竟然逐漸有了政治野心,“遂起逆謀,事發逃走,捕訪久之擒獲,斬之於市,並其黨十余人”。此事在《新唐書》裏做如此記載:“開耀元年……五月乙酉,常州人劉龍子謀反,伏誅。”對於官府來説,騙錢事小,但利用邪教有政治圖謀是大事,所以劉龍子在正史裏不是作為醫騙而是作為謀反之人留下了名字。
至於欺騙錢財的醫騙更是史不絕書。東晉葛洪《抱朴子內篇》卷9講述了一個故事:興古太守馬氏有親戚來投奔,窮困潦倒。而馬太守給支的招是讓他冒充醫生,對外詐稱是外來的神人道士,治病手到病除,“雲能令盲者登視,躄者即行。於是四方雲集,趨之如市”,很快獲利,錢帛堆積如山。一個毫無醫術的騙子何以能獲得如此成功,蓋因有一套控制群眾心理的辦法:“當告人言愈也,如此則必愈;若告人未愈者,則後終不愈也,道法正爾,不可不信。”即告訴患者,出外若有人問治療是否有效,則回答有效,若回答無效就真的無效了。成千上萬的患者在“信則靈”的心態擺佈下,真實信息交流完全阻斷,甘心情願地被分割成一個個信息孤島,成了真正的“烏合之眾”。這次成功的騙局具備了古今醫騙的所有特徵:事先造勢;製造從眾心理;造成患者之間的真實信息隔絕。
北齊時期的一次醫騙事件也具有類似的特點,尤其是在造勢上,使用了“醫托”,唐丘悅《三國典略》記載北齊武安一個妖人與其徒弟團夥行騙,辦法是弟子們偽裝成盲人及跛足人,號稱飲某處泉水,得金佛,其疾並愈。一時間北齊無論貴族、百姓均信以為真。偏巧水中有一隻老黃蛤蟆,乍出乍沒,人見之莫不以為神奇,就連齊武成帝高湛也率領百官前來飲泉水。騙子們偽裝成患者炒作造勢,再加上北齊社會風氣佞佛,所謂泉水中得金佛就是一次心理誘導,老黃蛤蟆的出現或者是人為,或者是巧合,但不管怎麼樣,這也是一次重重加碼,因為古漢語中蛤蟆就是蟾蜍,自古以來與嫦娥得不死藥奔月傳説相關,《抱朴子內篇》還把蛤蟆列為長生不老藥“五芝”之一,稱為“肉芝”:“肉芝者,謂萬歲蟾蜍”,既然如此,當然給了北齊民眾以極大的鼓舞,從皇帝到民眾趨之若鶩。
唐朝的皇帝們沒有北齊皇帝那麼荒唐,低層次的騙術他們是不會上當的,但是唐朝皇帝有一項家族傳統——服丹藥,可謂“矢志不渝,前仆後繼”,明文記載直接或者間接死於丹藥的多達六人,分別是太宗、憲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佔唐皇帝總數四分之一。其中有直接被毒死的,如太宗,亦有服丹藥後導致精神怪異引發謀殺的,例如憲宗、敬宗。為他們提供丹藥的術士,有的是真正相信自己的法術,有的則是不折不扣的騙子。
貞觀二十一年,唐特使王玄策借尼泊爾及吐蕃兵征服北天竺,帶回天竺方士那羅邇娑婆寐,該人自稱200歲,會煉長生不老藥,太宗此時年紀漸長,與很多君主一樣,早年間銳意進取,“我命由我不由天”,晚年則開始求助於各種神術,以求延年益壽,再加上一直有“風疾”(心腦血管疾病),所以輕信了這個“外來和尚”,服用其藥,不久駕崩。朝廷欲治天竺方士之罪,但“恐取笑戎狄而止”。
高宗時此神棍竟又來,再次提出為皇帝煉藥,李勣嘲笑曰:“此婆羅門今茲再來,容發衰白,已改于前,何能長生。”神棍不久在長安死去。
不僅造成皇帝死亡,術士騙子還會影響廟堂政治。中國古代很多莫名其妙的政治事件,在難以揣摩當事人動機時,不妨將視野投向左右。
唐憲宗時期曾有一個術士,不僅獲得了皇帝的信賴,而且在百官中享有盛譽,他間接導致本有可能徹底解決藩鎮問題的唐憲宗死亡,影響了歷史走向,最後自己落得身敗名裂。但他的威力即便在刑場上都有展現。
唐憲宗是唐代後期最有作為的皇帝,精力旺盛,對時事有較為明澈的把握,以“太宗之創業”、“玄宗之致理”為榜樣,重用武元衡、裴度、李愬等能臣,對藩鎮態度堅決,接連取得對藩鎮戰爭的勝利,使得桀驁不馴的河北三鎮相繼歸降,安史之亂之後困擾唐中央的割據問題一時間似乎結束。但是他壯年而死,使得這一大好局面在他死後不久煙消雲散,藩鎮復叛,此後直到唐朝滅亡,再無機會重振旗鼓。
唐憲宗的死與一個名叫柳泌的術士密切相關,柳泌本名楊仁晝,自小學習法術,逐漸小有名氣。唐憲宗後期越來越迷信長生不老,四處求不死仙藥,而宗正卿李道古先前在擔任鄂岳觀察使時候以貪婪殘暴著稱,非常擔心皇帝治罪,想盡辦法討皇帝歡心,他認得柳泌,並且迷信其法術,長期服用柳泌所煉製的丹藥,因此和宰相皇甫�一起向皇帝推薦。
唐憲宗接見了柳泌,讓他為自己和合丹藥。大臣裴潾堅決反對,《唐會要》卷56記載了裴潾《諫信用方士疏》,他認為,術士皆是騙子,真正的高人是出世的,哪有如此汲汲于名利者,要求以後推薦術士,藥成後術士及術士的推薦者先服一年,一年人體臨床試驗結束後再進人主:“《禮》曰:‘君之藥,臣先嘗之;親之藥,子先嘗之。’臣子一也,臣願所有金丹之藥,伏乞先令煉藥人及所薦之人,皆先服一年,以考其真偽,則自然明驗矣。”唐憲宗卻勃然大怒,貶裴潾為江陵令。柳泌與歷史上皇帝身邊的所有術士一樣有一套“話術”,專門應對丹藥無效的質疑,那就是為丹藥的有效性設置門檻,以此拖延時間。
《資治通鑒》卷240:“柳泌言于上曰:‘天台山神仙所聚,多靈草,臣雖知之,力不能致,誠得為彼長吏,庶幾可求。’”丹藥要想有效,必須到天台山採擷靈草,所以求為台州刺史。此事遭到很多人的反對,認為不能委任術士為一方大員。唐憲宗惱火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為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至此無人敢再反對。由是柳泌官拜台州刺史,賜服金紫。但丹藥仍然無效,柳泌恐慌,逃到山裏。“柳泌至台州,驅吏民採藥,歲余,無所得而懼,舉家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李道古保護之,上復使待詔翰林。”(《資治通鑒》卷241)在皇甫�、李道古的維護下,執迷不悟的唐憲宗最後寬恕了他,讓他進入翰林院。
根據韓愈《昭武校尉守左金吾衛將軍李公墓誌銘》記載,柳泌的手法是“燒水銀為不死藥”。具體的藥劑形態和服用方式不詳,但可以想見,唐憲宗可能同時面臨汞蒸氣吸入和長期的腸胃吸收,這是慢性汞中毒,會引發易興奮症、震顫和口腔炎等臨床表現,表現為性格改變,急躁、易怒或者膽怯、含羞、多疑等。唐憲宗就出現了明顯的症狀。“服其藥,日加躁渴。”(《資治通鑒》卷241)身體每況愈下,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竟以“餌金丹小不豫”,停罷一年一度的元日朝賀。之後多次不上朝,且表現得日益狂躁,身邊宦官往往成了發泄脾氣的主要對象,偏偏此時的宦官本就比較驕橫跋扈,不可能受此窩囊氣,終於,一個忍不下去的宦官陳弘志(又有史料記為陳弘慶)對皇帝動手,唐憲宗駕崩,享年43歲。“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庚子,暴崩于中和殿。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弒逆。”(《資治通鑒》卷241)司馬光《資治通鑒考異》:“實錄但雲‘上崩于大明宮之中和殿’。舊紀曰:‘時帝暴崩,皆言內官陳弘志弒逆,史氏諱而不書。’王守澄傳曰:‘憲宗疾大漸,內官陳弘慶等弒逆。憲宗英武,威德在人,內官秘之,不敢除討,但雲藥發暴崩。’新傳曰:‘守澄與內常侍陳弘志弒帝于中和殿。’裴廷裕東觀奏記雲:‘宣宗追恨光陵商臣之酷,郭太后亦以此暴崩。’然茲事曖昧,終不能測其虛實。故但雲暴崩。”
唐憲宗之死在歷史上謎團重重,《東觀奏記》中“光陵商臣之酷”一句借用楚成王子商臣殺害成王典故暗示子弒父,即憲宗為唐穆宗李恒所弒,背後有郭妃(郭子儀孫女)的參與。王夫之、呂思勉持類似看法。黃永年《唐元和後期黨爭與憲宗之死》認為殺憲宗即是為了保穆宗,所以“定冊立穆宗”的王守澄輩皆參與,這次政變同時也殺害了穆宗的政敵宦官吐突承璀和曾有希望繼承大統的酆王等人。而在後來《舊唐書》中則僅“中官陳弘慶(陳弘志)負弒逆之名”,為王守澄開脫。黃樓《唐代憲宗朝儲位之爭與憲宗之死——兼論穆宗“元和逆黨”説之不能成立》有不同看法,認為唐憲宗時期存在外臣與宦官的鬥爭,元和七年以翰林學士為核心的外臣取得了對宦官的階段性勝利,穆宗得登太子位,但到了元和十五年宦官集團又蠢蠢欲動,繼續謀劃擁立酆王,主使者不是吐突承璀而是另一個大宦官梁守謙。他認為事實真相如此:憲宗由於丹藥眼看命不久矣,酆王集團蠢蠢欲動,偏偏此時憲宗脾氣暴怒,引發了偶然事件——宦官王守澄和陳弘志衝動之下弒君,一時間宦官集團大亂,産生了兩派分歧,堅持追查誅逆的吐突承璀被另一個大宦官梁守謙所殺,梁守謙原本是酆王之黨,此時卻擔心追查會暴露自己以前與酆王之間的陰謀,於是殺死吐突承璀和酆王,掌控唐穆宗。
但不管是什麼觀點,學者都承認唐憲宗之死有一定的偶然性,以憲宗43歲之壯年,以一貫之睿智,假如沒有丹藥,不至於晚期政壇一片混亂,宦官對其動手也是衝動之舉,但被各派力量所利用。
至於對外宣佈,則稱憲宗為丹藥所誤,《資治通鑒》卷241:“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雲藥發,外人莫能明也。”《舊唐書》卷16《穆宗紀》直接説“上服之,日加躁渴,遽棄萬國”,把憲宗之死直接歸罪于柳泌。於是柳泌被扣押,此人諉過於李道古:“吾本無此心,是李道古教我,且雲壽四百歲(《舊唐書》卷135)”,最後被杖斃。可笑的是此時人們對其法術還心有忌憚,《舊唐書》卷135:“府吏防虞週密,恐其隱化;及解衣就誅,一無變異,但灸灼之瘢痕浹身而已。”害怕他使用隱身術遁去,殺死他的時候扒掉衣服,估計是為了看看是否會屍解,結果屍身沒什麼變化。“灸灼之瘢”要解釋一下,唐人最愛灸法,而且是直接灸,即艾柱放在體表灸,往往燙出水泡留下疤痕,唐人甚至以身上瘢痕為體檢指標,“浹”就是“周匝”,“但灸灼之瘢痕浹身而已”一句是諷刺柳泌,既然號為仙人,卻滿身灸瘢,可見是個百病纏身的騙子。
當年推薦柳泌的皇甫�被貶,死於貶所,至於李道古,他還真是個表裏如一的人,他是真相信柳泌的法術,所以仍舊服柳泌丹藥,“金吾以柳泌得罪,食泌藥,五十死海上。”(韓愈《故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按照韓愈的描述,迷信柳泌丹藥的還有很多人,柳泌死後繼續執迷不悟,例如他的侄孫女婿李于就是得到柳泌之藥後長期服用,柳泌死後他行為依舊,終於在長慶三年正月五日死於丹藥中毒。
上層社會,貪戀富貴,貪戀今生,而且波詭雲譎的政治鬥爭給他們一種朝不保夕的危機感,求助於各種法術也毫不奇怪,而在人治社會中,術士這種不起眼的小人物便借著影響頂層人物心智而影響了政局走向。
唐朝皇帝一代代受丹藥之害,推諉機制這種心理也一次次發揮作用,皇帝們並不得出“丹藥害人”的結論,而是認為服食方式不對,配方不對,禁忌不全……總之,不可能從整體上反對丹藥。《資治通鑒》卷248:“上(唐武宗)自秋冬以來,覺有疾,而術士以為換骨。上秘其事,外人但怪上希復遊獵,宰相奏事者亦不敢久留。詔罷來年正旦朝會。”武宗迷信丹藥,一病不起,但術士以“換骨”為理由繼續迷惑武宗。成語“脫胎換骨”本是道教詞彙,指服丹藥後胎、骨均煥然一新,然後成仙(或長生),《雲笈七簽�屍解部》:“雖功成道著,先未知道之時,積罪殃結,毀破肌膚,損傷骨脈。成就之後得蟬蛻,留皮換骨,隱跡岩穴,養骨髓,滋皮肉,千日方朝,五嶽受事,與前等同功也。”唐武宗的情況御醫和諸臣都無法掌握,最終導致武宗不治。古人認為脫胎換骨的過程與胎兒的孕育一樣需要時間,《雲笈七簽�金丹部》:“人以十月成身,丹以十月脫胎,人道相通,超凡入聖。”同書另一處提及服丹要滿前日,才可換骨。這也就是為何很多人服用丹藥明明已經出現不適但還要堅持的原因,他們認為脫胎換骨和蟬蛻一樣,是個緩慢而且痛苦的過程,需要忍耐。術士之所以可以騙錢,就是因為有這個“窗口期”。而唐武宗身邊的術士就是利用了這一點。一旦武宗死亡,估計他們又可以“屍解”為藉口,最終開溜。皇帝就這樣甘心受愚弄。
韓愈在《故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曾説:“余不知服食説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尚之益至,此其惑也!”他看似清醒,晚年卻也服起了丹藥,只是他認為前人的服用方式不對,要摸索一套自己的方法,於是給雞喂硫磺,然後吃雞,硫磺本不易中毒,但架不住長期服用,韓愈最後因此而死。白居易賦詩云:“退之服硫磺,一病訖不痊。”可悲可嘆。這種推諉機制是人類共通的心理,也給騙術留下了空間。
人類永遠不可能消除謊言與欺騙,但永遠要保持戒心。疾病戕害人體,謊言和騙術戕害人心,普通人憑藉一己之力也許對付不了病菌和病毒,但健康樂觀的心態、科學的頭腦,以及最重要的獨立思考的精神,能幫助我們抵禦謊言與騙術的襲擾。
(作者為陜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